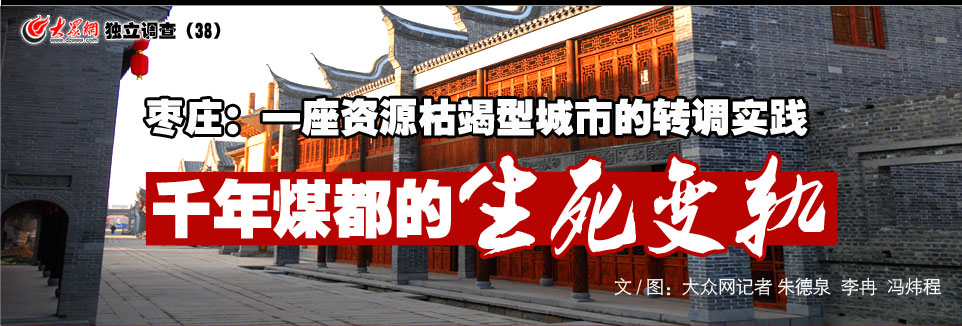|

馮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
當前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正處在一個以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為特征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有些專家對重化工業的提法有不同意見,包括我本人也不主張片面強調重化工業。在此只是指出了重化工業化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特點。目前,我國的重工業比重達到了70%,特別是2002年開始,重工業在工業產值、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2003年,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制造業對整個GDP的增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制造業可分為重制造業和輕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有16個百分點來自于輕制造業。從新興工業化國家走過的經驗來看,工業化進程基本上是從輕紡工業起步,進入重化工業的中期階段,之后進入后重化工業階段,最后進入知識經濟階段。日本在1955年至1975年實現了重化工業戰略,后來也面臨很多問題。1955年,日本的重工業的比重是45%,到了1970年,重工業自比重達到了62%。而聯邦德國1950年是61%,1970年達到了64%。從英國、美國等國家可以看出,在工業化中期階段,重工業占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總體上我們可以判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進入一個中后期階段。對于重工業比重的提高,我們最重要的是其形成機制是什么?新中國成立初期,重工業比重比現在還要高,但那時實行的一個戰略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學蘇聯模式,重積累輕消費,在產業結構上出現了“重工業重、輕工業輕”十分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1979年,我國工業化戰略思路發生轉變,就是實行消費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消費結構的升級,就成為影響工業結構內部變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來看,基本上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結構的變化導致了GDP總量的增加。
從結構上來看,1986年我國的制造業、工業部門,增加值居前幾位的是紡織、化工、煙草、石油和食品五個行業,其中有三個與居民的吃穿密切相關,那時的消費結構是為解決吃穿的基本需求問題。2003年至今,該結構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在工業增加值排序的前五個行業當中,第一是計真機、通訊設備制造,接下來的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然后是包括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石油工業。這五個行業對應消費結構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由吃穿向住行方面的升級。總體來看,我國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與日本、韓國、德國、美國相比,有所不同,帶有一定的時代特點和新技術特征,主要體現在重化工業發展的同時,電子通訊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因此帶有明顯的新技術條件下的特征。這是我們和新型的重化工業國家相異之處,既有重化工業的發展,也有電子及通訊設備的發展。
從不同產業來看,在中國的產業當中,出現了一些帶頭性產業和高增長產業群。決定于帶頭性產業的主要是三個因素,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快速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直接相關的產業,比如房地產、汽車制造,與城市化相關的基礎設施產業,與經濟全球化相關的一些產業,如電子通訊產業。在高增張產業群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帶頭產業。帶頭產業的產業鏈非常長,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進而形成了一批高增長產業群。
目前我國這種結構性的因素使得內生的經濟增長機制非常強。這樣一些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
我們既要看到內生經濟增長動力強這樣一個好處,同時也要看到并分析有此引發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分為短期風險和長期問題兩類。所謂短期風險就是經濟發展出現波動的風險加大,其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投資帶動投資。20世紀60年代,日本在重化工業戰略時期,投資帶動投資非常明顯,上下游產業鏈非常長,上游的投資帶動下游的投資。第二是重化工業本身具有自膨脹、內循環的特點,重化工業本身在產能擴張的同時,產生了比例較大的對自身產品的需求。比如鋼鐵產業,在其產能擴張時,對鋼鐵產品本身需求也很快,只有這樣才能支持產能的擴張。
我們初步判斷,像鋼鐵行業,它的自膨脹、內循環的量大概在20%—30%左右。在產能擴張時期,對自身產品的需求產生了,我們在判斷市場需求的時候,就要把建設期的短期需求和長期最終需求區分開來,避免受在短期能力擴張時期產生的虛假信號而發生誤判。
長期風險,就是資源與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十五”期間,我國的單位GDP能耗增長很快,1980—2000年,累計節能率是64%,而經合組織(OECD)國家同期是19%,全球的平均水平是20%,從中可以看到我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也就是所說的,用能源消費翻一番,來支撐國民經濟翻兩番。但是到了2002年以后,我們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長,“十五”期間,能源、彈性系數平均是1.03,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增長速度。“十一五”規劃提出,單位GDP要下降20%,這個目標現在看來具有相當大的挑戰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單位GDP能耗下降的情況還出現了反復。
目前主要國家的能源密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能源密度曲線是一個拋物線型的曲線。我們最關心它峰值出現在什么地方,單位GDP能耗的峰值出現在什么時期?美國出現在1920年左右,日本峰值出現在1974年,日本在1955冉1975年實行重化工業化戰略,日本在1974年經歷了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經濟受到了嚴重沖擊。后來,日本通過調整結構,發展高附加值的裝備制造業、組裝工業。
第二,越接近現代,峰值越低。比如日本,它的單位GDP能耗最高的時候,只有美國的一半,其原因在于技術進步的因素。基于20世紀60年代的技術,日本實現工業化,用了比美國單位GDP能耗一半的水平來完成了它的工業化。美國的峰值也英國低,德國北美國還要低,工業化越往后,越接近現代。單位GDP能耗的峰值水平就越低,主要還是技術上的影有。這樣就會帶來一個疑問,我國“十一五”提出的單位GDP能耗下降20%能不能實現?有人說:我國GBP占世界的4%,煤炭消耗占到30%,其他資源消耗也占到很大比例,也有人說中國的單位GDP能耗是日本的5倍,美國的3.5倍等等這樣一些數據。我認為這樣的比較不具可比性,且夸大了我國的節能潛力,為便于橫向比較,我用了產品能耗進行對比,即同樣生產一種產品,中國消耗多少能源?美國消耗多少能源,世界最好水平消耗多少能源?火電的能耗我們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4%,水泥的綜合能耗高44%等。八個主要耗能工業,2000年單位產品的能耗均比國外高46%,2007年這一差距降到了20%。節能潛力仍然是巨大的,而節能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技術節能,二是結構節能,近一段時間,通過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和關閉規模小的生產能力,取得了一定的節能成效,但真正的考驗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以及技術的實質性進步,這就意味著要走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路徑依賴問題,如果分析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單位GDP能耗的橫向對比,可以發現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的依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美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就比日本高得多,而且近40年沒有發展根本性變化,也就意味著存在著路徑依賴的問題,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旦鎖定一個模式,幾十年難以改變,日本就是鎖定在能效水平很高的路徑上。
產生路徑依賴的關鍵時期主要有三個快速發展時期。第一是快速工業化時期,第二是快速城市化時期,第三是居行民消費結構快速升級時期。尤其是第二、第三個因素十分關鍵,一旦消費模式鎖定和城市化模式鎖定,這個國家的發展路徑也會鎖定,就會產生路徑依賴問題。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在第三個快速發展化時期,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從長期的問題來看,第二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持續的競爭能力問題。分析貿易競爭力的定量指標,一個是貿易競爭力指數,還有一個就是顯示比較優勢指數。這個值越高,就表明競爭力越強;值越低,競爭力越弱。顯示比較優勢的指數在2.5以上,我們稱之為有競爭力,絕大多數行業是在2以下,沒有什么競爭力。而有競爭力的像紡織、皮革制品,從年度來看,競爭力在逐漸下降。這樣,如何維護好既有比較優勢,以及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就是一項十分緊迫且需要破題的問題,中央提出來建立創新型國家,這是實現我國競爭戰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可以說,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戰略,要從過去單純的消費導向型戰略,轉到創新驅動型戰略,要著眼于培育競爭的新優勢。從產業結構的變化來看,要實行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發展戰略性新型產業并舉的方針,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是一篇大文章,產業鏈升級、價值鏈提升有著巨大的潛力,也是實現效率增長的重要途徑。
——摘自《30位著名經濟學家會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