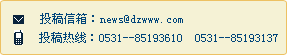劉盛蘭是招遠市蠶莊鎮柳杭村一位普通的農民,現年90歲。屬鎮分散供養的“五保”老人。自1996年起,劉盛蘭靠拾荒資助全國各地貧困學生近百名,資助金額達到5萬多元。就在劉盛蘭大把大把往外寄錢的同時,自己卻過著如同乞丐一樣的生活。他穿的衣服都是許多年前的,而且一年就冬夏兩套,吃的菜都是從菜市場里撿的爛了的土豆、蘿卜。許多好心人和志愿者來看望他,為他捐錢捐物,他一分不留又全部資助了學生。別人都以為劉盛蘭活得苦,但劉盛蘭覺得自己活得很安心。
“好人有好報”,“捐得越多就越高興。”“錢再多也沒有什么用,人是無價寶”這些是劉盛蘭常掛在嘴邊的話。他的事跡先后被煙臺、山東等多家電視臺,煙臺日報、煙臺晚報、齊魯晚報等多家報紙報道,2011年,新浪網對劉盛蘭老人的先進事跡進行了轉摘,7月份,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慕名來到蠶莊鎮,對劉盛蘭老人進行了專門采訪,12月14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播放了劉盛蘭老人的先進事跡……。2004年劉盛蘭榮獲“感動”煙臺年度人物,2011年,劉盛蘭榮獲煙臺市“道德模范”,是遠近聞名的助人為樂模范人物。
撿破爛資助上百貧困生



在招遠,有這樣一位老人,吃得是撿回來的爛菜葉,穿得是自己親手縫的粗布衣服,住得是破爛不堪的房子……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老人,在17年的時間里,用自己撿破爛的收入,先后資助了上百名貧困生。他,就是年過90的耄耋老人劉盛蘭。
一次偶然的機會,劉盛蘭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救助報道,從那時起,他就將自己微薄的收入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學生,也逐漸從周邊幾個地市拓展到全國各地。
劉盛蘭的侄外甥劉昭江告訴記者,把積蓄都捐出去后,原本就非常節儉的劉盛蘭只能從集市上撿別人丟棄的白菜、土豆、茄子等蔬菜以供日常生活,這一撿就是17年。劉盛蘭對自己很“摳門”,但在給學生捐錢這方面,卻很大方。最多的時候,他同時資助著50多名學生。
雖然街坊四鄰和親戚們時常給他帶點吃的,但老人還是從不舍得多吃一口。前不久,煙臺一家公司的老總了解到劉盛蘭的情況后,直接派人給他送了六千塊錢,“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條上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在老人家里,記者發現了一摞嶄新的匯款單,劉盛蘭告訴記者,最近他又為河北的一對兄弟捐助了2000元。看著老人手中的一大摞捐款回執單,記者數了一下,有一百多張,每次匯款金額在200到500元間,最多的一次2000元。與之對應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受捐助者收到匯款后寄來的回信。
“我真希望他們收到錢后給我回個信。但也有不給回信的,我就覺得有點不踏實。”劉盛蘭說著隨手拿起一張放在炕上的報紙,指著一則報道告訴記者:“這里面寫著一個女孩需要錢才能繼續念書,我匯了300塊錢,但至今沒給我回信,我真的想知道,那300塊錢到了沒有。”
“錢不重要,人才是無價之寶。”這是劉盛蘭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如今的劉盛蘭已是年過90的耄耋老人,考慮到老人的年齡跟實際狀況,當地政府、民政部門曾多次做工作要老人到敬老院安享晚年,但這個“犟老頭”不為所動。因為不去養老院,他可拿到每年1800元的生活補貼。如今,劉盛蘭還供著四個孩子上學,“一對黑龍江的姐妹,一對廣西的兄弟。”老人表示,只要條件允許,他的這一行為將繼續持續下去,直至不能動為止。
劉盛蘭:八旬翁拾荒資助百名兒童
在山東省招遠市一個小村莊里,有一位89歲的貧窮老人劉盛蘭,他17年幾乎未嘗肉味,沒添過一件新衣,“吝嗇”的連一個饅頭都舍不得買;可正是這個倔老頭,卻在貧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將所有錢財捐給了全國各地的貧困學子。
“他干的都是積德事兒,但日子卻過得連要飯的都不如。”劉盛蘭的親友如是說。
·17年他幾乎全靠拾荒過活
蠶莊鎮柳杭村,與招遠市其他金礦資源豐富的地方相比,這里著實算不上一個很富裕的村莊。
“劉盛蘭親戚知道他住哪兒。”村中央一間不起眼的小賣部里,在店老板的指引下,劉盛蘭的侄外甥劉昭江帶著記者來到村頭一條小胡同外,“老人就住這里面。”
推開大門,院子里幾株辣椒長勢正旺,一棵榆樹下則堆滿了廢舊酒瓶。劉昭江推開房門,屋里除了一張堆著破舊棉被的炕和幾個老箱子外,就剩下積滿灰塵的表彰綬帶、相框以及摔壞的獎杯,再無他物。
劉盛蘭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年近九十的他,黝黑干瘦的臉上布滿粗粗的皺紋。正是這個黑瘦的老人,將自己一輩子的積蓄,都捐給了貧困學生。而自己17年來幾乎都是依靠撿拾別人丟棄在垃圾堆里的蔬菜過活。
·最多時他同時資助50多名學生
一次偶然的機會,劉盛蘭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救助報道,從那時起,73歲的他就將自己微薄的工資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學生,也逐漸從周邊幾個地市“擴張”到全國各地。
把所有積蓄都捐出去后,原本就非常節儉的劉盛蘭只能從集市上撿別人丟棄的白菜、土豆、茄子等蔬菜以供日常生活,這一撿就是將近17年。“那些東西其實都能吃;要是看到有被丟了的鞋子,我就撿來縫縫再穿。”劉昭江告訴記者,從給學生捐錢開始,老人就幾乎沒嘗過肉味。
劉盛蘭對自己很“摳門”,但在給學生捐錢這方面,卻很大方。最多的時候,他同時資助著50多名學生。微薄的工資也讓他在資助學生時力不從心。“300塊錢的工資沒辦法分給50個人,我只好這個月寄給這個,下個月寄給那個,一個個的輪著給。”
·為捐助學生拒進養老院
雖然現在街坊四鄰和親戚們時常給他帶點吃的,但老人還是從不舍得多吃一口。唯一的改善,就是每天到村頭去買一兩個饅頭,偶爾喝碗豆漿。
前不久,煙臺一家公司的老總了解到劉盛蘭的情況后,直接派人給他送了六千塊錢,“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條上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為多點錢捐助學生,劉盛蘭一直沒進養老院,因為不去養老院,他可拿到每年1800元的生活補貼。“我是一個子兒都不剩了,全捐了,捐了好,捐了幫學生念書。”現在,劉盛蘭說他只能供四個孩子上學,“一對黑龍江的姐妹,一對廣西的兄弟。”
有時候,劉盛蘭還會在村里撿些酒瓶子,院子里那棵榆樹下成堆的酒瓶子,都是他撿來的,“現在很少有人收了,價錢也便宜了,不過總歸能換點錢。”
記者臨走前掀開了老人家灶臺上的鍋蓋,鍋里面放著四個碗,一碗是中午吃剩下的面條,一碗咸菜,一碗已蒸過多次的茄子,還有兩個油餅。也正是這兩個油餅,竟引起了劉昭江的好奇:“誰給你的油餅?”
“隔壁給的。”劉盛蘭高興地把盤子端起來給我們看了看。
·最有價值的家當:回信和匯款單
劉盛蘭臥室的墻上,一個深藍色布袋里,裝滿了匯款單和回信,這是他唯一看重的東西。他取下布袋將里面的匯款單和信件都倒在炕上,又另從床頭下找出了一些。“我也不記得匯出去多少錢、收了多少封信。”
記者數了一下,僅匯款單就有一百多張,每次匯款金額在200到500元間,最多的一次1000元。與之對應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受捐助者收到匯款后寄來的回信。
“我真希望他們收到錢后給我回個信。”劉盛蘭希望知道自己匯出去的錢,對方已收到。“但也有不給回信的,我就覺得有點不踏實。”劉盛蘭說著隨手拿起一張放在炕上的報紙,指著一則報道告訴記者:“這里面寫著一個女孩需要錢才能繼續念書,我就匯了300塊錢,但至今沒給我回信,我真的只想知道,那300塊錢到了沒有。”
·討來的欠薪也全部捐出
劉盛蘭之前曾在招遠市當地的一家公司里看門,每月能掙三百來塊錢。不過隨著公司生意的不景氣,到后來就一直沒給他發工資。“拖了整三年,一萬多塊錢的工資幾乎一分沒給。”待劉盛蘭準備離開公司時,那家公司老板只給了他三百元錢,之后就再沒提工資的事,盡管多次討要,一直未果。最終,劉盛蘭走上了法庭,那一年,他82歲。
“官司贏了我就去要錢,但經理就是賴著不給。”劉盛蘭回憶說,之后他幾乎每天都到公司去討要欠款,但公司經理卻一直告訴他:“沒錢”。
幸運的是,劉盛蘭在市長接訪日那天遇到了當地法院的一位主任。“那個主任一聽我的情況,就趕緊找到法院的執行局。”最終,在法院執行局的多次干涉下,劉盛蘭才分兩次要回那一萬余元的欠款。
不過,錢剛到手不久,便被劉盛蘭全“揮霍”了。“全捐出去了,我留著也沒用,捐給學生念書救急,怎么不比自己花強?”
·認死理兒的倔老頭 干的都是積德事兒
“我們完全不能理解他,他這一輩都不知道圖什么?”結束對劉盛蘭的采訪后,劉昭江告訴記者,家里人對劉盛蘭的做法一直很不理解,都覺得劉盛蘭是自己找罪受。“倔,倔的不得了,認死理兒。”
街坊鄰居們也都覺得,老頭子活這些年,到頭來還是一無所有,怎么都覺得不是那么回事。“干的都是積德事兒,但自己的日子卻過得連要飯的都不如。”
如今,劉盛蘭很少出門,一是因為年紀大了,再則偶爾會有不相識的人來看看他,“沒一個認識的,很多都是帶著老婆孩子來的,說是來看我。我捐過誰,我也不記得了,他們愿意來看我就來。”
![]()
大眾網版權與免責聲明
1、大眾網所有內容的版權均屬于作者或頁面內聲明的版權人。未經大眾網的書面許可,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將大眾網的各項資源轉載、復制、編輯或發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場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資訊散發給其他方,不可把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務器或文檔中作鏡像復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眾網的任何資源。若有意轉載本站信息資料,必需取得大眾網書面授權。
2、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大眾網”。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3、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大眾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本網轉載其他媒體之稿件,意在為公眾提供免費服務。如稿件版權單位或個人不想在本網發布,可與本網聯系,本網視情況可立即將其撤除。
4、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聯系的,請30日內進行。